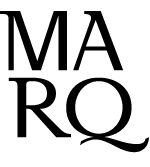[電影] 諾亞方舟
在我逃離就讀七年的私立基督教學校後,我便非常厭惡任何聖經故事改編的電影。第一個理由是受不了基督教這個宗教,第二則是因為就學時就看很多,離開了就更是不想被洗腦。但當曾經執導《真愛永恆》、《黑天鵝》、《迷上癮》等結合寫實、魔幻、與宗教符號的經典電影的戴倫亞洛諾夫斯基宣布改編聖經中“諾亞方舟”的故事時,我的心仍不免雀躍不已。我相信亞洛諾夫斯基絕不會像其他導演一般甘於一板一眼的歌頌基督教派裡制式的美德。 果然,《諾亞方舟》這部片雖然取材自聖經裡諾亞攜帶妻小打造方舟,帶領全世界的動物避開上帝降下的洪水的故事,但劇中對原本的故事大作改動,甚至於發展出完全不同的人物與主題。對於我這個無神論者來說,這樣的改變自然歡迎之至。但我發現亞洛諾夫斯基並沒有背離聖經裡的想法,反而很適當的在無神論與有神論中找尋了一個適當的避風港,讓觀眾自己去適應。但這並不代表亞洛諾夫斯基畏縮在中立的觀點裡。作為一個出色的導演,他也為自己適當的發出聲音。 我想,不管是東方人還是西方人對諾亞方舟的故事應該多少都有所理解。遠古世界裡,人類深重的罪孽導致上帝決定要以洪水滅絕全人類,唯獨留下心底善良的諾亞和他的家人。上帝要求諾亞建造能容納世界上每一種動物(各兩隻)的方舟,並告訴他在洪水來臨前動物們會自己上船。就這樣,諾亞帶著自己的家人日以繼夜的打造史無前例的巨大船隻。起初所有人都笑他瘋了,不過諾亞仍堅持造船、風雨無阻。最後動物們從四面八方來到諾亞的方舟上,洪水也淹沒了大地。諾亞在海上漂流到萬念俱灰,透過一隻白鴿才找到了陸地,重新繁衍人類。這就是我們所知道的諾亞方舟。戴倫亞洛諾夫斯基的諾亞方舟一樣有上帝、天使、伊甸圓、亞當與夏娃等等聖經裡的人事物,但他並不帶入基督教直接的教義,反而以一種任何文化皆適宜的手法去解釋創造論。例如,整部電影中從未以上帝或是神來稱呼上帝,反而以“造物者”來稱呼創造世界的大能。天使墮落到凡間,作為懲罰而被岩石包覆全身,成為初民的守護者幫助人類等等橋段也是電影新加的。但亞洛諾夫斯基並不以墮天使稱呼他們,反而以“保衛者”稱之。順帶一提,聖經裡墮天使應該直接去地獄,但電影裡反而沒有提及地獄這個地方。 戴倫亞洛諾夫斯基的諾亞方舟裡融合了許多不同宗教的思想和符號,其中猶太教、基督教、和卡巴拉系猶太教最為深入。《諾亞方舟》確實是個宗教色彩濃厚的電影,但他絕不是一個宗教電影。它大致上遵循原來聖經故事的框架,但加入了更多邏輯及反思。其中最大的命題就是人與信仰的衝突。電影中,諾亞為了遵循造物者的吩咐,拋棄了自己的理智和家人的感情,追求完全的侍奉信仰。可是這樣的行為在電影裡造成了全家人很大的衝突,甚至到了以命相搏的地步。觀眾不得不反問:這樣好嗎?為了自己的信仰一意孤行會不會太魯莽了? 聖經裡對於諾亞的家人其實著墨甚少。他們在整篇故事裡並沒有表現出特別反對或支持的立場。但在電影裡諾亞的家人都有各自的心思、立場、及動機。雖然他們敬愛諾亞,但當他喪心病狂的執著於造物主的指令時,他們也不得不想辦法抵抗。飾演諾亞妻子的珍妮佛康納利在這部電影裡非常出色,將母親、女性、及妻子的不同觀點和想法演繹的淋漓盡致,尤其一場為了孩子的存亡與諾亞爭執不下的戲更是讓人驚豔。羅素克洛完全是好萊塢鐵漢柔情派的代表人物,不過他自從《神鬼戰士》以後基本上都在演同一個角色,諾亞這個角色基本上亦然。演是演的很好,只不過我們都已經很熟悉他的表演方式了,所以並沒有被他所感動。 戴倫亞洛諾夫斯基的視覺表現一直都很出色,而他最擅長的灰色系冷冽視覺在諾亞方舟裡更得到強烈的提升。縱然在一望無際的荒涼史前文明,他也能表現出蒼涼的美感。 撇除《諾亞方舟》這個故事來自於基督教聖經裡之外,戴倫亞洛諾夫斯基的《諾亞方舟》應可被視為一個全新、甚至完全不一樣的獨立故事。它厲害的地方就在於不管你是有神論者還是無神論者、基督徒還是佛教徒,它所探討的信仰層面是廣泛且平易近人的。就算你只是想好好看一個史詩動作片,他也能滿足你的欲望。(石頭人大戰人類這種戲碼夠史詩了吧!)觀眾不需要被宗教的預設價值所綁縛,有空就趕快進戲院看看這部最不聖經的聖經電影吧。 – John Wang
Read article